放大资金,增加盈利可能
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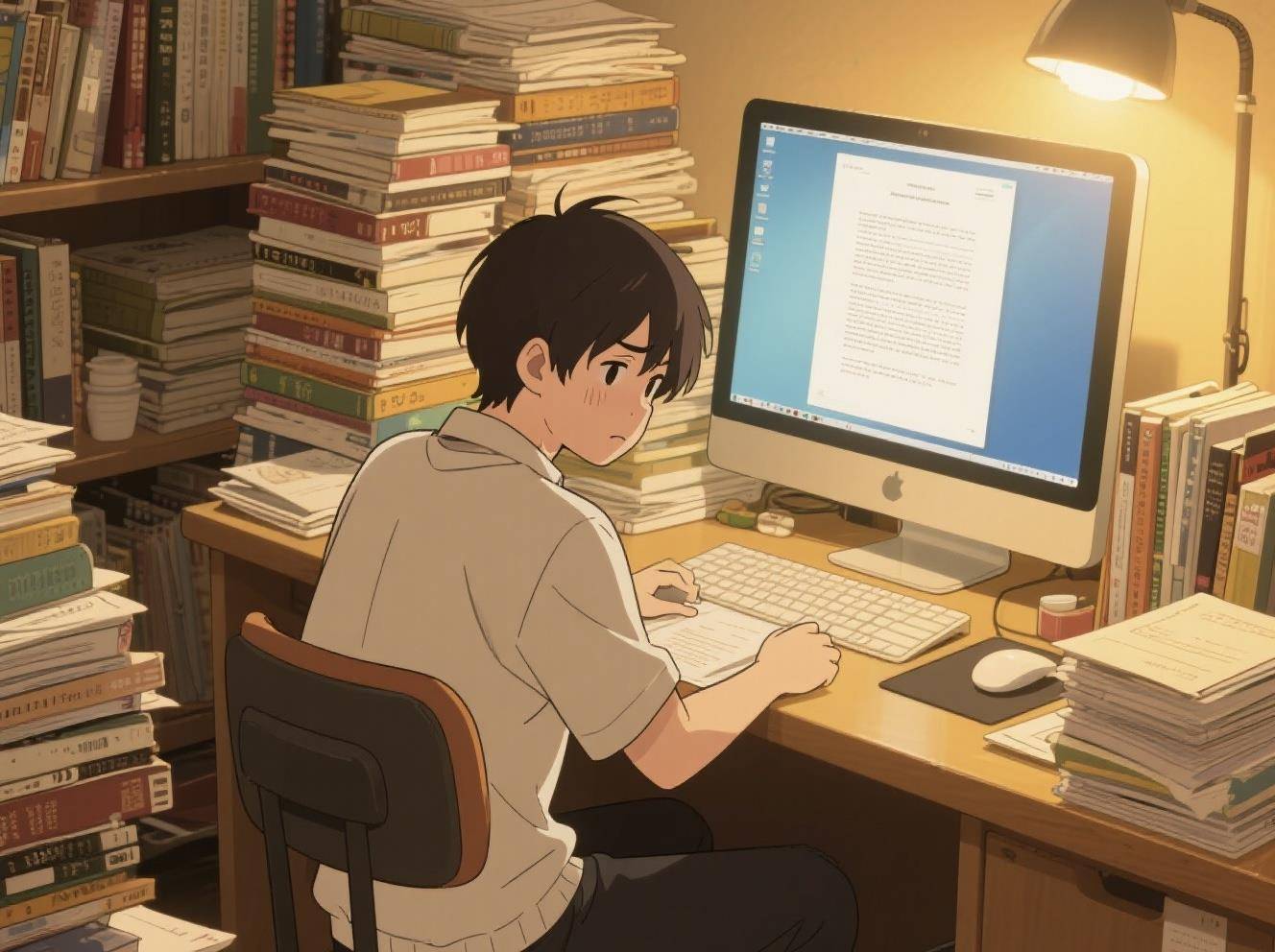 图片由AI生成
图片由AI生成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要求导师为学生论文署名这件事上,国内多所应用学科比较强势的“双一流”高校,都推出了相似的明文规定。
一名985高校的工科教授认为,虽然论文主要是学生写的,但学生在学校做的东西往往是导师团队承担的某个大项目中的一部分,知识产权都归学校,“老师做通讯(作者)也是正常的”。他所在的学校也以理工科为主。
另有一位文科专业的博士表示:“但对文科来说,很多思辨性的研究也不需要一个团队去做,可能一个人就能完成。”他还提到:“因为理工科有设置通讯作者,能让导师在论文中获得比较高的认可,而文科的文章基本只认第一作者,即便有通讯作者,大家也是一样,无形中就会涉及排位问题。”
应该说,他们对于论文署名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标明论文作者身份的重要方式,署名是对作者研究成果负责的体现,理应按照贡献大小进行排序。从一些高校强制要求导师为学生的论文署名的规定来看,或许是为了引导学生融入学术共同体,通过导师署名来强化指导责任。然而,当强制署名成为学生能否毕业、发文的“硬通货”而非学术贡献的自然表征,其逻辑便悄然异化。
无论导师是否踏入过实验室,无论思想火花是否源于学生独立迸发,署名权一旦成为导师的“红利”,便容易滑向“学术寻租”的边缘。正如一位文科专业博士生导师所言,如若导师没有参与论文的讨论、写作,或者进行指导,署名“肯定不合适”,但无奈学校规定在前,“我们也没办法”。这种“无奈”的背后,是按学术贡献署名的“人之常理”在行政规定前的低头。
某种意义上,强制署名扭曲了学术的本真价值。真正的学术尊严,奠基于实实在在的探索与贡献;导师是否署名,是署一作还是二作,也应源于切实的培养之功。把论文署名变成一种不讲实际贡献的强制规定,把导师名字当成论文质量的“信用背书”甚至潜在免责保险,只会让学术评价陷入形式主义的迷雾之中。导师的署名权似乎被兑换成了资源与保障的砝码,而学生真正的智力贡献却被稀释或遮蔽。
对学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做学问要实事求是,署名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与其用强制署名制造虚假的“师生共同体”,不如回归学术本源。理应强化实质指导和过程监督,完善导师职责评价体系,让署名权真正成为学术贡献的自然结晶而非一刀切的行政指令。
配资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